回眸清漳远帆
汤毓贤
云山苍苍,漳水泱泱,人类逐水而居。漳州这座城市的最初,即从云霄绥安溪发源衍生。自初唐起始,绥安溪易名为漳江,延用了上党清漳河的名称。这是中原移垦者情系原乡故土,把他乡化故乡视作义无反顾的忠君爱国情怀。我少时喜爱漳江,缘于时而渡船对岸走走下坂亲戚。当时江上无人采沙,也没有造桥。摆渡篷顶西林船过溪,无异于出门旅游,获得兜风观景的享受。长大后才知道,原来家里吃用水源悉数来自漳江。听老人们说,南北江水闸未建时,漳江是受潮汐影响的。虽说遇涨潮乘坐渡船,可感受摆渡者持桨搏浪;但倘碰上退潮,则可于清澈见浅的河床捞上蛤蜊,有时还需提鞋拎起裤管,淌水踏沙登上码头,那才叫惬意呢!
一
有谁知道,“漳水云山”过去还是两广至闽南边陲北境。大禹治水时,闽南与岭东今潮汕大地原野属于天下九州的扬州。秦始皇三十三年岭南平定,临海百粤地设立南海郡。汉兴秦亡时,秦将赵佗趁势据守盘陀岭以南古越地,呈表要求敕封南越王。刘邦鉴于汉初政权未稳,管辖南越鞭长莫及,只得准其所请。于是原处海陬古揭阳县地、今云霄北境火田江溪通海、水系发达、船运通联的“云山”,就成了南越国北疆。时有官员和外商水陆过往,又是高官流放、履新和返朝之必经。火田拜岳与葛布两山之间后埔庐仔坑村地带,有来自盘陀岭峡梁山脉络支派的水源,汇归于丘陵腹地越王潭。南越王赵建德曾于潭中“伐木为船”,操控的船舶能“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,往若飘风,去则难从。”到晋义熙九年,“云山”置县绥安,边邑重镇安仁辖属义安郡。隋开皇十一年,海阳县城建置潮州,以绥安县为边邑。大业三年罢州复郡,改为潮阳郡,唐武德四年再称潮州。而福建开发较晚,南朝陈永定年间才独立置州,称闽州、丰州、建州、泉州和武荣州等。“泉州”本为福州使用,治在晋安郡闽县冶城。泉、潮两州边邑“云山”地属岭南道,以梁山蒲葵关为边界。跨过这道高岭险隘的关隘,往南连接粤东丘陵。长期的军事和政治隔阻,构成闽粤文化分水岭,山南山北风俗的迥异,使云霄平原与潮文化水乳交融,古老的潮音仍唱响漳江两岸。
云山潮湿的肥原沃土,滋养了原始先民。闽南粤东百越人巢居崖处,以射猎耕山、捕食鱼类为生,处于刀耕火耨的原始游动农业状态。先民每年选择一片山地焚烧林木作肥料,用石刀或青铜工具凿坑播种旱稻、黍稷等作物,秋后收成。两三年后肥土消失,另择山林焚烧播种,形成了火田这一村名,即史家何乔远释义的“火田畲也,凡畲惟种黍稷,皆火耨”是也!汉武帝平闽后,认为闽越地为“叛服无常”的荒服之国,就直接委任旧秦汉族郡长强化统治。但这种重汉臣作法,容易由地方暴政激发民变,造成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。迨唐太宗统一全国,仍称闽粤割据“遗孽未殄”;高宗即位后,委任归德将军陈政率中原府兵、军眷共87姓进屯云霄,平息“蛮獠啸乱”事件。
云山百越路,市井十洲人。中原府兵南来前,古绥安县地旷人稀、连年无雪、到处行春,是泉潮流移汉族与山越人口杂处区域。受东西交通和开放环境影响,云山重镇安仁自由贸易区仍处于闲散无序状态。在大唐朝贡政治和对外商贸体制下,执玉入贡北上来朝的海外番邦使臣、路往商贸交易者热络于道。商肆既有各色人等集中边贸,又有中东等番船涉海循溪岸交易,形成以“十洲人”为特征的番商集市。边贸商路的通畅,是东西物资传输互动、各取所需的必然结果;而社会经济发展除满足家庭有所盈余,则为建州立县提供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基础。
二
陈元光创立漳州前,绥安故城已是闽南政治、军事和商业中心,造船、水运诸业发达。漳江东注东山湾,是汉唐番邦使者循广州港北上时,首处有港澳停泊、市集交易的商品集散地,充溢的水利条件是建郡立城的首选,也是拓展对外航运的天然港澳。来自波斯湾的番邦商船取道海上丝绸之路,经红海进印度洋,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广东沿海,再循漳江口驶往边邑集市自由贸易颇为寻常。而以中原移民为主形成的闽南人,也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影响最大的族群,被称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马车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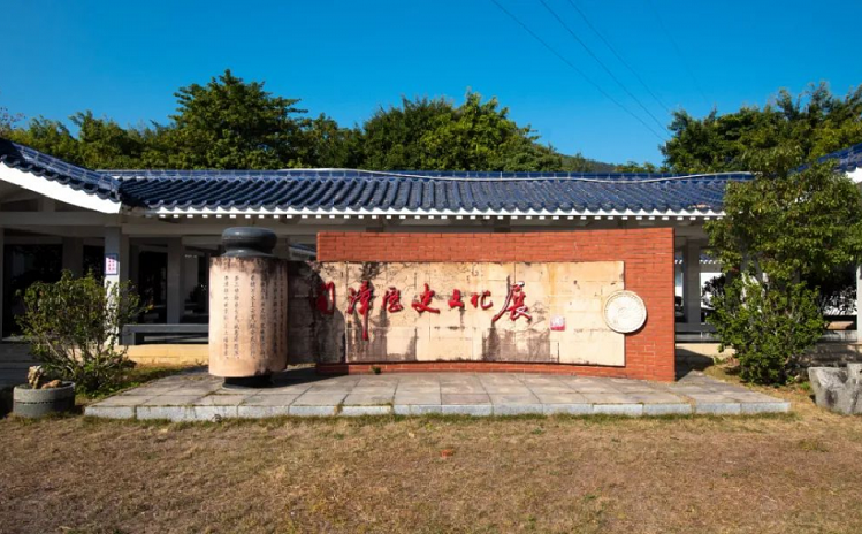
开漳历史文化展
明黄仲昭《八闽通志·山川》有一则番商轶事,言及漳州创建前两年,陈元光开屯建堡区域有中东商人康没遮从广州来闽南经商,在温源溪温泉出水口投10钱沐浴,成为温泉涨溢活跃的真实纪录。垂拱二年,陈元光疏请革去绥安县,从潮州到泉州各割一部分,取边邑安仁为中心新建漳州及属县漳浦、怀恩,并率僚属拓展往西北峒寨和潮州通道,又兴修水利、造船通航、兴陶冶矿、通商惠工,同时开发海岛滩涂,经营近海渔盐,以“海舶近通盐”实现“财用以阜”。番商们携带来数量可观的走私香药前来贸易,此后香药、甲香和海舶,也就变成著称朝野的漳州土特产。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,朝廷才允准漳州海舶兴贩香料。《大明漳州府志》云:“初唐建州,自常赋外,仅贡鲛皮、甲香而已”,数量为“贡鲛鱼皮二十张,甲香五斤。”出现本土兴贩陶瓷、丝锦与兽皮,外商贩买珠宝、香药和鱼皮的自由市集,漳江上中游水域对外商贸之繁盛可见一斑。
公元9世纪,阿拉伯地理学家胡尔达兹比赫《道理邦国志》列举唐朝4大贸易港,并载述沿途经济物产和风土人情等,除了今“鲁金”越南河内,还有“汉府”广州、“刚突”扬州和“汉久”或以方言谐音译称“建久”的漳州。他说“建久”距“汉府”航程8天,即指濒临漳江、直通大海的古漳州云霄港埠。漳州建置后仅过百年,州治经历自梁山西南往李澳川、龙溪县2次迁移,但海内外商船货运,还是延续频繁地往返于漳江沿岸船坞码头。南唐保大年间,有一位据称是开漳将帅李伯瑶后裔、三佛齐国镇国李将军到此运香货易钱后捐建将军山普贤院,还委请知州延僧住持兼顾开漳始祖陈政墓祭祀香火。《龙溪县志》称:“南唐保大中,有三佛齐国将军李某以香货诣本州易钱,营造普贤院,手书法堂梁上。元丰年间,僧喜麟摹其墨迹以示人,无能知者。”三佛齐国地处中西海上交通咽喉,系7~13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古国,三分之一国人经商。该国有梵文和用梵文所写的南海语2种文字,普贤院法堂梁上手笔可能属于后一种。宋《诸蕃志·三佛齐国》载:“太平兴国五年,其王夏池遣使茶龙眉来。是年潮州言: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、犀角、象牙至海口。会风势不便,飘船六十日至潮州,其香药悉送广州。”这位蕃商李甫诲就是营造普贤院的人。
宋代漳州自造船只,繁盛的漳江是海外诸国经商活跃的埠头。皇祐间有晋江籍林昭庆率商运往返于广西、天津等。他将财产委托同事赡养双亲,徒手到云霄汤泉山临济寺(今火田岩仔山)受戒皈依,圆寂后葬于溪边山。漳江澳进出船运除南通东西洋,也开始有北方航贸。云霄渡头窑、许厝窑、黄峰窑、水头窑和七里铺窑等所烧“宋洞仔”小瓮,常装腌菜品配船运销北方港埠,促进瓷业兴盛和航运发展。
三
为征关税充入国库,宋廷鼓励东南沿海对外开放经商,远行东南亚和阿拉伯进行贸易,随之江溪纵横的漳江中游又兴起航运码头,商贸活动逐步转移到水静深港的月溪。港尾埠之北有宿舟泊船的静澳称溪门,沿岸有商船业中心集镇敦照。元丰五年,葭州岛设黄墩盐运栈,专营集盐解运。绍兴间,漳浦县六都安仁乡浦东里云霄设临水驿驻佐官西尉,今莆美中柱敦上设敦照所,分驻县尉管理商运、开发漳江港尾埠澳。随着敦照集镇的崛起,不少民户从上游向西南转移,增加了人口负荷。乾道三年诏设云霄铺,驻铺军于望高山下。绍定间增置西尉,有县尉叶炜、杨左莅任。县尉为省道州郡监管,行使征收船舶、盐务、商务、关税等职责,形成漳南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口岸,堪称漳浦次县治。
元朝为远征东南亚在漳州大造战船,发展了漳江造船业,多处造船场坊陆续开办。至元六年,漳州路总管同知陈君用为防御沿海寇患,移驻古郡县西林建石城堡设防,赋予老集镇新的生机。陈君用进驻西林后,擒北洋海盗杨奴、破汀州山寇罗天麟、邓师公于白花岭,降潮寇夏山虎而屡建大功,才议设云霄镇城。至治间,西林城西南望高山东南麓设置云霄驿并派驻驿丞。元末明初月溪淤塞,民户从敦照集镇北徙,不少船商弃月溪转迁异地,部分循西林城而来。西林的人口暴涨,使得南北人流汇聚于漳江冲积平原发展新集镇,终于催生云霄镇城的崛起。清《漳浦县志·方域志》称,云霄港在六都,埔尾港在六都,上坑港在六都,中寨港在六都,4大海港分踞漳江两岸。云霄港俗称“状元港”,专营航运的船头行北通津沪称“上北”,南达港粤和远通诸番为“下南”,东至台湾叫“过横”“横洋”,历风浪、海盗和战乱犹兴盛不衰。
云霄东厦船场村,自古是修船造舰坞头,隋炀帝曾派员于此澳湾处建造海船。明永乐十五年五月,三保太监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避风东山湾,驶入漳江港尾埠等港澳补给,并在云霄大坑、马山、上坑采伐格木修造船舰;在大墩、厚地、蠔潭招募航海能手,留下郑和碑及供奉太保公史迹。随着元末泉州港衰落和郑和下西洋中止,官方贸易基本停止,但漳、泉民间对外贸易仍风风火火。云霄商船队“以土特产驰远国易其方物,博利而乐”,在东南海面频繁活动,造就了海商巨贾的崛起。永乐十四年仲春,云阳方氏第六世方民清随族人货船出航,偶于滨海古雷沙滩拾到一盏番船灯。这是遭劫遇难的番船遗物,于是在巡检司严究下蒙冤惹祸。但他只有13岁,父亲方英代子解京服刑,将家事托付其弟方明大。方明大初得一子,执意替兄承判顶罪,不料途遇地方疫情,解差失散,遂隐居浙江舟山。其妻曾氏在兄嫂关顾下殖孤方民旭成人,留下“孝思之本、兄友弟恭”佳话。
步人明中叶,朝廷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而厉行海禁,封杀了出海贩运和对外交往,但仍有冒禁出洋市贩者用走私维持海上贸易。成化、弘治时,民间海上贸易以武装走私形式达到高峰,数云霄吴永绥为代表的“海客”家族最为显贵。林偕春《云山居士集》称,嘉靖、隆庆间,漳浦、云霄、铜山等地“往往有藉饷船而私至日本者,或始以日本而终以西洋”“番船岁出,其入市吾邑也,内则直至云霄、旧镇。”历隆庆元年,穆宗宣布允许私人合法远贩东西洋,至17世纪大航海时代中后期,郑氏海上集团控制马六甲海峡和南海航线。清初统一台湾后,涌现乾隆间高文杰等家底殷实的海商富豪。清中后期,云霄对外对台商船达百余艘,又出现驰骋海上、突破海禁的朱濆等海商。嘉庆后,侨居东南亚各国的云霄人带着明月辉映下无尽的乡愁省亲回乡,不少“客头”行商运入南洋诸商品,返回时运销陶瓷等特产。此时的云霄设饷馆,从台湾运进稻米称“台运”,后改民间商船运输。光绪十一年,云霄商船跟台湾淡水、基隆、高雄、安平4口岸贸易频繁。此外,云霄下普庵、火田瑞堂村、阳下村等处,先后出土16世纪西班牙银币、越南“景盛通宝”、吕宋银饼等;嘉庆间霞港关帝庙碑刻、道光间古河口镇高塘寅饯寺墨书梁签,分别载有商船号与捐银额,都印证云霄拓展中外与闽台商缘。
漳江如同九龙江和晋江一样,都是哺育闽南人的母亲河、孕育闽南文化的摇篮。在我看来,清澈见底的江溪、香甜爽口的江水,犹如慈母乳汁,滋润着一方土地和生灵。跨越千年时空变幻,时光老人展示的漳江竟然如此神奇!如今,初唐诗人张循之描绘的“市井十洲人”的景观早已不复存在,但漳江航运的兴衰,却为自唐初以降漳州拓展对外航运写下海丝文化的瑰丽华章,成为古代漳州拓展海外贸易繁荣的缩影。
(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、省作协“走进八闽”文化采风系列之《走进云宵》;图片来源于云宵新闻网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)


